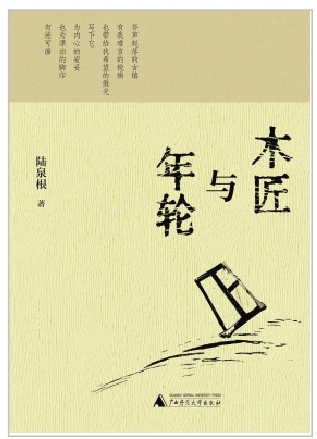
《木匠与年轮》 陆泉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2月
陆泉根
父亲畏寒。冬天,胃痛常常不请自到。胃是父亲的软肋,痛得厉害的时候,父亲会捂着肚子,蜷成一团。父亲有自知之明,他不和寒冷硬抗,老老实实穿上那件有块大补丁但厚实无比的灰棉袄。
穿上灰棉袄的父亲不再怕冷,能安心地坐在家里等电。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是父亲锯木厂的命根子——能让锯木机轰鸣,能把原木剖成板材,能赚钱养家。电依旧未到,着急的父亲在昏暗的屋里踱来踱去,不停抽着卷烟,手指忽明忽暗地飞舞着。窗外,雪悄悄落下,不多时,大地成了一张巨大的空白试卷,而父亲像极了一位急着赶考的人。学生苦读,父亲苦做——要过年了,置年货、攒学费,什么都要花钱。“电来了!”父亲赶紧起身,掐灭烟头,带上门出去。踩着积雪,父亲的脚下发出“噗嗤”的声响。
在家的母亲会算着父亲回来的时辰,提前用煤油炉煨一锅粥。天亮,父亲推门进来,拍掉满身的雪,端起粥碗,嘴沿着碗边转了一圈。呼呼。呼呼。胃里一股暖流,父亲身上便有了暖意。喝完粥,父亲从腰间掏出皱巴巴的钞票递给母亲——他一夜的劳动所得。
还是寒冬。读大一的我放假回家,母亲让我去锯木厂叫父亲多扛些废木柴回来。父亲在锯木,抱着大木头的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带锯,灰棉袄被扔在一旁。天冷飕飕的,父亲的鼻尖挂着清水鼻涕。锯好木头,看见我,父亲用手抹了鼻涕,轻声说:“回来了!”我顺手把旁边的棉袄递了过去。父亲脸上充满暖意。
父亲到底没有敌得过寒冬,十二年前,在一个最冷的天气走了,母亲煨的热粥也没有顾得上喝。祭日,母亲盛一碗米饭,堆得高尖尖的,摆在父亲的遗像前——那是古镇穷人最寻常的祭奠。自责的母亲,常给我讲父亲的故事——都和冬天有关。而我,父亲的儿子,在城里的睡梦里,常常遇见父亲:锯木、收割、抽烟、学车……醒来后却寻找不见——作为写作者,作为父亲的儿子,我怕那些记忆终有一天湮没在时光的深处,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记下他的故事,写一本书,用来铭记、用来怀念。这本书,我当它是一碗温热的稠粥,献给我那一生辛劳沧桑的父亲。
写不下去,我就枯坐在电脑前,努力地回忆父亲。“父亲”很配合地从我的脑海里跳出来,和我聊着那些陈年往事。我想起来,当年厂里生意还没有清淡的时候,父亲就忙里偷闲地给我打了一套结婚用的组合家具。我记得他遇到了坎儿,他坐在一堆白坯木料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眉头紧锁,像极了写作时对着电脑发呆的我。父亲没有放弃,慢慢地琢磨,最后竟真的打出了一套漂亮的家具。省下几百块钱是小事,他得对得起“木匠”这个称号。
书的题目《木匠与年轮》,是作家萧易替我取的。我是他亲二叔。书稿我们探讨了很久。萧易离开故乡二十年,对我父亲和那片土地,我们有相同的情感和认知。“木匠”是父亲的身份,也是他一生坚守的手艺;“年轮”是木材的纹路,也是每个生命的轨迹。“木匠”和“年轮”,两个寻常却又意蕴丰富的意象,就这样约好后出现在书的封面。
书稿交给广西师大出版社,编辑继续打磨,就像我的父亲打磨家具,结结实实,充满木头的温度和香味。这本书里,木匠父亲当仁不让,统领着一个又一个独立成篇却彼此呼应的故事:对家人的牵挂、对生活的执着,还有钝痛。无尽的钝痛,属于父亲,属于我,也属于天下所有的儿子。相信,藏在文字里的微光,能够照亮我以后的每个寒冬夜晚。
人生的季节里,总有猝不及防的寒流:新书还未到手,母亲——那个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家煨粥的人突然离世。我有些手足无措。好在文字成了我对抗悲伤的有力武器。那些重新鲜活起来的人与事,最终都把悲伤变成了一种力量,牵着我在城里的冬天回忆。故乡、老屋、炊烟以及父亲踩雪时发出的噗噗声——一圈一圈,像树的年轮。一个老木匠其实就是一棵老树。
对我们家而言,最寒冷的冬天早已过去,但我依旧会在每个冬天想起父亲。捧起书,我总觉得父亲就在身边:穿着灰棉袄,拿着斧头,不是在干活就是走在干活的路上。我看到了父亲的尊严与执着、隐痛与期盼,还有他在风雪里前行的背影。这本书是交给时光的试卷,也是献给父亲的祭品。它菲薄,像母亲烹煮的那锅米粥,朴素而温热。
我必须写下去。为父亲、为亲人,也为我自己——就像作家庞余亮在书序里讲的:“永恸之诗从来不会停止,唯有继续书写,才能找到那把时光深处的斧头,而木匠父亲,会在儿子的文字里重新诞生。”
岁末,这个寒冷的时节,我又一次想起父亲——其实,父亲从未走远,他在儿子的心里,也在《木匠与年轮》这本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