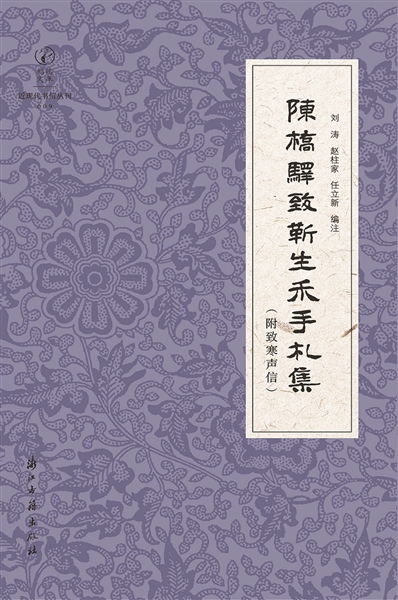
《陈桥驿致靳生禾手札集(附致寒声信)》 刘涛 赵柱家 任立新 编注 2023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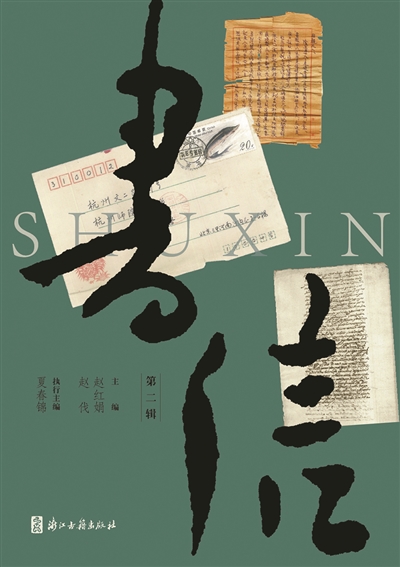
《书信(第二辑)》 赵红娟 赵伐 主编 夏春锦 执行主编 2023年10月

《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信》 杨斌 编 2021年7月
孙科镂
作为一名图书编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书信的编校与出版成了我工作的一大重心,续写那些泛黄信笺背后的掌故与温度。
记得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想,书信之于当下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书信是陌生的,因为忙碌的我们早已习惯了拿起手机,拨个电话,发个语音,或者在即时聊天软件的对话框里,简单打上几行字,再添一两个卡通表情,点击“发送”,就把事情交代了过去。在这样的生活节奏里,写信显得老派。
但书信也是熟悉的。因为相比于其他文体,书信的写作状态往往更自由,文字也便最真实。鲁迅先生在为孔另境《当代文人尺牍钞》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就曾指出,从作者的书信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简洁的注释。”而正是这种自然的流露,使得即便是与写信人素昧平生的我们,也总能轻易地在书信中寻找到情感的共鸣。
刚刚走过一个新岁之交,从手头的这几本书信集里翻检出这些辞旧迎新的内容,读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总算结束了一年的工作”
每逢岁末,回顾一年的工作,无论成功大于失败,抑或坎坷多于完满,总归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而1992年的最后一天,年近古稀的陈桥驿先生在给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靳生禾的信中,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因颈椎骨质增生影响供血不足,住院两月,内人随着住院则有照顾方便原因在内。十月底出院,事情连续不断,在家未有三五日的停留。最后一个节目是复旦大学博士生答辩,昨天下午从上海返杭,总算结束了一年的工作。而正在此时,读您来信,不胜快慰也。
两人的书信往来大抵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此后延续三十余年,直至陈桥驿先生辞世前一年。对于靳生禾而言,陈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良师益友;而在陈先生眼里,靳生禾则是一位值得“寄予厚望”的历史地理学者。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亲密的关系,陈桥驿先生在致靳生禾的书信中总会有一种特别的坦率。在岁末年初的信中,他会抱怨,“暑假后一直忙于外出,到最近才安顿下来,但年后恐怕又要奔走,不胜苦恼也”(1991年12月30日);也会慨叹,“今年写序又在十篇以上,索序者多半是学生,实有无法谢绝者,为之奈何”(1992年12月31日);更会烦恼于,“今年出差已有十多次,虽每次对方都派医护,毕竟老朽,难以为继。今日下午,因绍兴一座大公园开幕,碑记是我撰文并书,不得不去”(2008年12月26日)。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在谈及陈桥驿先生晚年繁忙的工作时,曾不由得赞叹:“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一项很少有人能超越的纪录。”其实读读这些珍贵的书信,我们明白,所谓的奇迹与纪录背后,也有着每个人都会遭遇的身不由己的无奈,既不必讳言,也无须回避。只不过在无奈之外,总少不了一份学人的担当与坚持。所以不论一年多么繁忙,还是要加上一句“总算结束了一年的工作”,作为自我的宽慰与鼓励。
“惟乐天知命而已”
随着年岁的增长,迎新春的喜悦之外,渐渐掺杂进的是对岁月无情的喟叹。1997年年初,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在致《光明日报》编辑韩小蕙的信中谈及友人的离世,心绪难平:
最近曹禺、端木等等摆脱了烦恼,我周围也走了一些人,有的还不到六十岁,多少影响一些情绪。
而2006年,已年届八十三岁高龄的来先生在1月5日致友人冀有贵的信中,面对自身的衰老,倒更多了几分坦荡:
不佞自八十以后日非一日,体力见衰,目力尤眊,看字写字更为困难,全仗手势熟悉。匆匆数十年,不知老之已至,惟乐天知命而已。
人们似乎总是更愿意在书信中与挚友一诉衷肠,所以辞旧迎新之际,“老之已至”“乐天知命”的话题才会被反复提及。1996年年初,杨绛代病重的钱钟书先生致信学生马成生,便不无遗憾地期许:“西湖草长莺飞,正是晴雨皆宜的好地方,不胜神往,但我们老病,无缘作游春之梦,容待异日吧。”1997年年底,台湾著名作家、小说《城南旧事》的作者林海音在给她的忘年交、竹刻艺术家叶瑜荪寄去的新年贺卡中,这样写道:“我们(指林海音及其丈夫何凡)分别与风湿、糖尿长期抗战中。祝你新年快乐,子恺漫画馆进行顺利!”其中自然是无奈有之,达观亦有之。
于是,面对生活,我倒觉得,来新夏先生在1995年岁末写给韩小蕙的另一封信中透露的“独家秘诀”,别有趣味:
我最近有所发明,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新的参悟。一个中心:力奔小康。两个基本点:身体健康点,精神愉快点。独得之秘,不可外传。
“自然要与他们一起前进”
其实,面对岁月无情的变迁,个人的“乐天知命”只是一种向内的选择。而万物复苏之际,人们想到的另一个词,大概是未来。1984年12月底,《中国美学史》的作者、年逾六十的刘纲纪先生在致李泽厚的信中,回顾一年来自己与年轻人的交往,这样说道:
这里已组成青年美学研讨会,定期活动。第一次会上我讲了一下,总觉马克思之精深博大至今未为世人所知,憾甚!故又唠叨一通,青年们或视我为保守僵化也说不定。但看来他们还视我为可与一谈的“师长”,即此足矣!
之所以对年轻人报以极大的期望,并乐此不疲,理由其实也很简单——“中国正处于剧烈变化中,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此深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完成此种变革,自只有青年们足以当之”。
在刘纲纪看来,尽管青年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稚嫩与不足,但他们身上却带着一种可爱的坦率以及朴素的是非观,“无论如何,他们终究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也因此,“要与他们一起前进”,就显得格外自然,而“能为之鸣锣开道”,亦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至于“冯唐易老”的喟叹,实在是那么微不足道。
四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重读这些文字,依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还记得设计《书信(第二辑)》宣传页的时候,我和主编一起草拟了好几套推荐语,其中一句是“在不写信的年代,我们更容易被书信所打动”。这句话最终被我们选择放在了页首。其实,书信的价值远不止寻求情感与思想的共鸣而已,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点却最具有普泛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