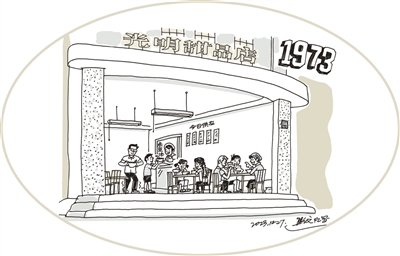
这一年,海丰西餐社叫“光明甜品店”,人们喜欢夏天去吃一碗冰凉的赤豆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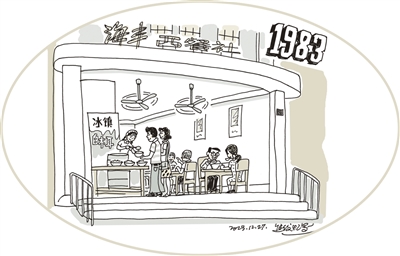
冰镇白木耳放在店门口的桌子上,吸引行人驻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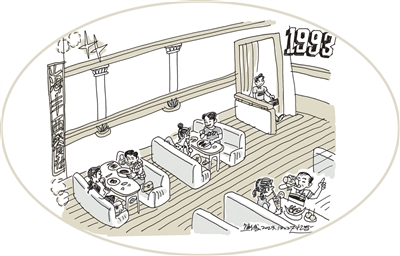
直奔二楼,对罗宋汤和黑椒牛排印象很深。刀和叉怎么用,很多人还弄不清楚,不过也并不重要。 本版绘图:焦俊

这个年末,西湖边一家穿越百年历史的老餐厅要重开的消息,让“老杭州们”惊喜不已,像一位息影多年的电影明星又要重新出山。
孙昌建
1
一转眼又到年末,灵隐寺的挂历一换,那就是辞旧迎新了。前几天严寒恰逢牙疼,戴着口罩过闹市便咬牙切齿的,好像跟谁都有仇似的,于是去看了半年多未见的两位牙医老友,决定来一场口腔内的“扫黑除恶”。这两位是牙医中写诗最好的,因为牙医中写小说和说脱口秀最好的是余华,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口腔科出来又去看了冬至从深圳返杭扫墓的老友,他问我:大学路图书馆又开了吗?海丰西餐社又开了吗?然后他说到了那些从没有吃过老杭帮菜的都在写杭帮菜。于是我们俩吃着外卖,长吁短叹。他长吁是因为不仅在南国吃不到正宗的炒二冬,到了杭州还是吃不到;我短叹是因为牙疼,更是因为有颇多感慨,正如有时拍遍栏杆,江山无限,却找不到共享单车的停车处。
时光倒退回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的杭州还是窈窕少女,倚着西湖含情脉脉。我在参加工作时,曾经有两个小心愿,一是坐遍杭州的公交车线路,一是吃遍杭州的大小饭店。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愿,是因为那时年轻,只要努力一下,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到了“老大徒伤悲”的今天,再回首去复盘坐过的车、吃过的菜,既不能说乏善可陈,也不敢说美轮美奂。岁月这把“杀猪刀”实在是很锋利的。
2
为什么要说那时的杭州城是窈窕少女?因为跟今天相比,她的确不是太丰满。
我对那个年代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是上档次的宾馆饭店都是美食的大本营,如人们心心念念的怡口乐,就是以杭州饭店(香格里拉饭店)为依傍的;二是那时新冒出来的社会化餐馆,基本分布在南北向的延安路主道上,并向体育场路、武林路以及湖滨路、环城西路、保俶路等呈星火燎原之势。一言以波风水门蔽之,都在市中心。包括后来兴起的著名打卡地白鹿面馆,就是深藏在百货大楼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想想那时能够上“百大”吃一顿饭,一定是很重要且很隆重的,请客的和被请的都觉得很有面子,被请的可以记叨一年,请客的一定是又拉到了一个大客户。
那时国营的老牌餐饮店,都是名气和好评兼而有之,如楼外楼,如杭州酒家,所以杭州日报副刊也时常跟这些店家搞活动。虽然那个时候也并没有觉得西湖醋鱼好吃到天上去,但我要提醒大家,那时我们还没有吃过剁椒鱼头和臭鳜鱼,千岛湖鱼头的名气也还没攻占杭城,我们的味蕾还基本处于基因带来的一花独放之势,那时我们还刚刚从糖醋排骨、红烧狮子头、千张包和鲫鱼豆腐汤起步,所以当看到“天天渔港”饭店那鱼池中千奇百怪的鱼时,好像有一点到了香港的味道。
是的,“天天渔港”“食为先”“高朋”“喜乐”“望族”“阳光”,这一些知名酒店已经挂在了那时我们的嘴上。它们中多数已经进入了历史,而这样的历史可能更多的是口述史,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像海丰西餐社这样又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实在是少之又数,正如一位电影明星,息影多年又重新出山,她的未来我们还不可预知,而她的过去能让我们津津乐道。但我们所说的“过去”,除了有时间的界定之外,它一定也是有空间概念的。那时去萧山吃饭,一定是去吃喜酒,而不是像今天是去打卡。
3
我是1993年从乡下进城到平海路上班的,在那里一干就是五年。单位没有食堂,出门左转走七步就是一个酒家,今天还在,没有大名气,生意依旧;再走七步就到了吴山路口的宁波汤团店,我偏爱咸汤团,那汤团里面的肉,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良心。至于说海丰西餐社,那属于更早的记忆了,走个三百步左右也到了。
今天当我们说起海丰西餐社,实际上是在说时尚,说记忆,说我们跟新鲜事物的接触和接受方式。接受有两种,一种是文化上的接受,一种是味觉上的接受;正如爱也有两种,一种是精神之爱,一种是身体之爱,如果能将那两者合而为一,当然是至臻至美了。今天当我们说起海丰,我想提供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牙医阿贝说的,他说那时在海丰买一杯牛奶,三下五除二就喝光了。但我们共同的朋友、电力工人德华说走时一定要剩一点的,要不然很没面子的。另一个细节是它的二楼有个餐厅,我偏好那里,因为它清静且干净,且有点西式的调性,菜品中似有一个咖喱鸡块,由此我也爱上了跟鸡块搭档的土豆,这是我以前是不喜欢的,正如包心菜,当包心菜一进入罗宋汤,连同胡萝卜,档次一下子就提高了。
是的,当今天我们讲起海丰西餐社,实际上可能是在说它隔壁的那个书店,书店里的那个女营业员。我清楚地记得,1986年的某一天,我和牙医阿贝大夫就是在那个书店里看到有一本《朦胧诗精选》,那时还没有开架售书,每一本书都要让营业员拿出来的;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近视,戴个眼镜也只是假装近视以显得有文化,装着装着就真的近视了,至于最后有没有文化,好像急需书店开出一张证明。
翻开那本诗选,跳过北岛、蔡其矫、杜云燮、舒婷等一批诗人的名字,最后发现了孙昌建的名字,那有他的两首发在《诗歌报》上的小诗。我当即买下两本,一本给自己,一本给阿贝。阿贝马上说要请我吃饭,当时去了海丰还是金城饭店,我忘了。这几十年间吃了朋友不下几十顿的饭之后,我的牙齿终于吃坏了,也终于成了牙医朋友的“客户”,正如阿贝的师父易老师当年给丰子恺口中“剿匪”一样。但我不能跟丰老师相比,丰老师过生日是还要请易牙医到楼外楼吃饭,这一点我今天做不到了,我今天如果要请朋友吃饭,想来想去要么是“宝中宝”,要么是“福缘居”,或者是“三姐妹”“弄堂里”,要么是“老头油爆虾”,要么是诗人朋友张锋开的“兰桂江南”。张锋当年在读高中时,杭州日报副刊就两次集束发表他的诗歌。现在想来成名太早也不好,今天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老张是谁了。
4
所以当今天有人说要怀念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包括怀念那时的美食,我就要笑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才二三十岁,荷尔蒙正春风激荡的时候,那当然是最好的。那是个穿风衣的年代,不管有没有风,也不管是不是穿风衣的身材,几个朋友裹挟着风和风衣走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朝我的平海路走来,那是很有周润发港片的味道的。
是的,平海路上有平海池,解放路上有湘海池。你的第一杯酸梅汤、果子露是不是在平海路喝的?那是去怡口乐的预热阶段。《诗刊》和《收获》是在斜对面的报刊门市部买的。澡堂里谈诗,钱柜里唱流行歌曲,这就是坦诚相见,三观一致。所谓老朋友,就是见面不需要拥抱,分手不需要说再见,只要谁微信上说一句,晚上到“德明”或者“黄龙大排档”,那二话不说,我戴上口罩就出发了,这一出发,既是怀旧,又是迎新,而且是迎着风向前,正如某一首歌所唱的那样。
